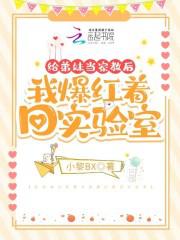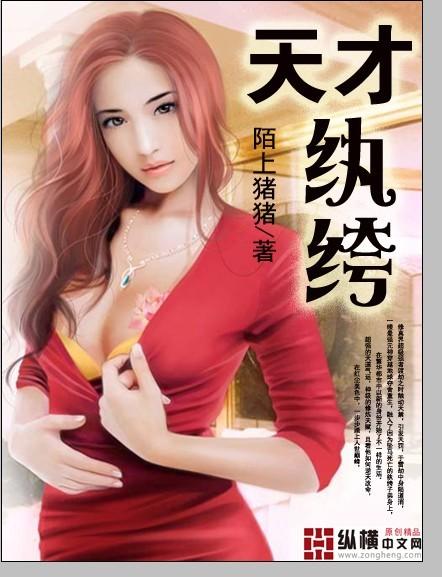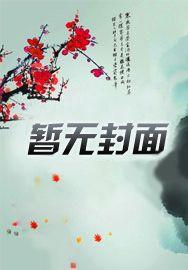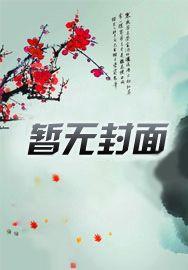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两百零二章 被遗忘的时光(第2页)
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一场景的起笔和收笔都是迎风飘扬的英国国旗,那么上面的读解就不应该被指责为“过度诠释”了吧?——其实,父子关系经常在叙事艺术中充当历史转义的修辞功能。但是,只有在港岛这样特殊的地方,因为先后由殖民历史和冷战格局造成对自我身份的创伤性经验、以及文化认同上的深刻危机,作为历史转义的父子恩怨才会在极大程度上服从于兄弟情仇的情节模式,以把无法接续的历史干脆表现为断裂的当下。
然后是精神分析与叙事的可能。
“被遗忘的时光”这主题歌,真的是把时间和记忆的主题贯穿在《无间道》三部曲的始终了。然而,这歌并不是画外声源的怀旧氛围的点染,而是内在于故事情节的具有戏剧动作性的构成元素——母宁说,它在时间、记忆甚至怀旧之外,提供了另一重要主题的原型:即改写。先是在《无间道》里,阿仁哥把刘sir与韩深密谈的录音刻录在这歌的光盘里面,送给他的妻子mary;而到了《终极无间》里,杨锦荣则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方法让刘sir原形毕露。
实际上,在《终极无间》里,改写这一主题以多种变奏形式出现。也就是说,重要的不再是改写的内容,而是改写——更准确说,是叙事本身。因为改写身份记忆之于刘sir,就和写报告之于杨锦荣、精神分析之于李心儿一样,都是对叙事行为本质的疑虑和探询。
最为有趣的一场戏,是李心儿医生对着她的两个病人——阿仁哥和刘sir——述说,她曾经如何通过改写记忆,来退避自己犯下过错之后的羞耻感;然后,她特意解释道,这种被压抑的记忆(“被遗忘的时光”)只要能够讲出来,就可以得到抒解。
这段精神分析的自我倾诉,其实正好表征了这部影片关于叙事的自反性的思考。因为对于刘sir而言,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他的问题绝无可能凭借倾诉得到解决。就决定他生命历程的那些事来说,一旦做出选择,像韩深最开始所说的那样:“你们自己选啦!”就注定要“没的选择”。对刘sir来说,叙事对时间(或者所谓“命数”)的抗拒仍然是作为一个问题,而远非答桉,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刘sir竭力改写自我身份当然是《终极无间》的情节主线:他从镜子中看到的自我形象是阿仁哥,而他向李心儿许诺要亲手逮捕的刘sir却被投射到了杨锦荣的身上。
但是,刘sir对自己身份、对真实自我的困惑,在《前传》中就已确定:在向倪家告密说mary是杀死倪父的幕后真凶之后,他以一种迷茫而疑惧的目光紧紧盯着反光镜里自己卑鄙的模样。如果说在这套三部曲的前两部影片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对刘sir这个人物的刻画——对他的人格究竟怎样得以形成的来龙去脉进行追索;那么到了《终极无间》里,他的身份、他的真实的自我其实已无悬念,导演呈现给观众的只是他对自己这一身份、这一自我的徒劳的改写过程。
应该承认,杨锦荣和沉澄这两个新的人物的加入,在编剧技巧上构成了置换前一个悬念的新的悬念,他们两人身份的可疑促成了观影快感的新一轮延宕,好象不到最后的高潮段落这一谜底不能真的揭破。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很早就已“暴露”给观众了:当刘sir第一次潜入保安部安装监视器时,楼道里就响起了腿已瘸了的沉澄特有的脚步声。
由李心儿的精神分析所提示的叙事本身的可能性,在刘sir那里实在很难成立。他也并非没有倾诉,他把自己“是韩深的人”这一事实告诉了李心儿——但是这无济于事。
并不是所有创伤都能够通过修订记忆来抚平的,并不是所有事实仅仅通过叙事就能变得顺理成章。讲述或者倾诉确乎能实现一种想象性的解决;然而同时,这种解决也必然提供真实以一种再现性的呈现。这不仅是刘sir的困境,母宁说这其实正是精神分析自身的困境:一种关于叙事模式的困境。精神分析作为临床实践,端赖对话双方的主体间关系,倾诉不过是转移了症候,使之在一个新的语境中显影。
当你的倾听者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当你的倾诉因那个对象的缺席而无法得到反馈,当你失去了那个对话的另一主体——准确说,失去了那个在符号界不断借他人的躯壳而显灵的他者,那么你的想象就永远不能应合于符号秩序,永远不能获得一个为这一秩序所认可的社会身份,你的贵乏的自我就不能从对话过程所实现的身份指认中得到任何补偿。
这何止是刘sir这个人物的困境?他对自己身份记忆的徒劳的改写,难道不正暗喻着身处港岛文化认同危机之中的电影作者所面临的主体位置的两难选择?
对于这部影片的叙事者来说,他们的倾听者、他们的对话对象、他们的观众究竟是谁——港岛,还是母亲?就港岛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论,母亲显然不是那个适当的人选;但与此同时,母亲毫无疑问又扮演着最重要的他者形象。在港岛与母亲之间,就是想象界与符号界断裂的地方,就是只有“必是非常潜能”的主体才能游走其中的无间道。
逢此历史际遇,对于作为港岛文化认同最主要载体的电影生产,叙事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这是《终极无间》提出给影片自身的难题,其困扰形成一种无意识的症状也显现在影片的体征上。
那个精神分析的诊疗室,确乎可以被视为一个由主体自我他者所构成的叙事自反的场景。这一场戏里,尤其令人疑惑的,是阿仁哥和刘sir共同分享着李心儿的催眠的那个画面。这当然是一个想象性的场景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无法确定,那究竟出自谁的想象?是李心儿面对刘sir时,脑海里仍然时刻浮现着阿仁哥的挥之不去的印象?还是刘sir希望通过阿仁哥的幽灵在自己身上附体,来改写他的自我、改写他的身份记忆?
他把阿仁哥作为理想自我的投射,的确是贯穿整个影片的情节线索;然而从镜头语言上,我们很难相信上述场景会是出自刘sir的想象,因为他和阿仁哥始终分享着画面空间,也即分享着意义空间。这和整部影片的基本配置是相一致的:刘sir和阿仁哥都是被叙客体。从李心儿的角度上,这种含混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这一叙事段落是以她对阿仁哥的回忆开始、也是以她对阿仁哥的回忆结束的
特别是最后,黑白画面(阿仁哥说:“过了今天就没事了。”)直接转而为彩色画面,(李心儿的)心理空间直接转换为(以阿仁哥为行动主体的)故事层面,这表明李心儿的视角参与了影片的叙事,特别是主导着这一段落的叙事。
但另一方面,刘sir和阿仁哥所共享的画面却不是由李心儿的视点提供的——镜头从门外进入(这是一个瞬间的画框构图),越过李心儿的头顶,推进到阿仁哥和刘sir的双人中景,这显然是真正的影片叙事者的视点。另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一场景里在李心儿和她的病人之间没有形成任何真正的对切镜头——换言之,李心儿和刘sir都是在对着想象中的对象自说自话,他们彼此都不是对方的适当的对话人选。
至于阿仁哥,尽管他显然从未成为影片内的叙事者,但他始终是叙事和镜头的焦点,许多段落都是由聚焦于他这个人物的怀旧式目光开始的。一个有趣的段落是,在接受诊疗期间的无数次插科打诨之后,黑画面上先出现“第……次见面”的字幕,然后亮起定格画面,稍停,画面开始运动,阿仁哥与李心儿热吻——这样的剪辑(电影艺术最重要的改写也即叙事手段)把这一场景完全处理成了想象。但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这是谁的想象?阿仁哥,还是叙事者?
通过以上粗浅的分析,笔者想要指出的是:《终极无间》的导演所面临的根本的叙事困境,是他无法找到切入影片内部的叙事视点。他无法真正地认同于剧情中的行动者(无论是刘sir还是阿仁哥),也不能附身于故事中的旁观者(李心儿)
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他的主体位置的悬而未决造成的。他或可游弋于这三个人物所能提供的视点之间,但是他绝无可能弥合横亘于叙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那道裂隙,因为恰恰是回忆本身阻断了任何的这样一种认同关系,也就从根本上阻断了插叙、倒叙等叙事手法和隐藏起摄影机位置的流畅剪辑之间暗相契合的真正可能。
就象刘sir之于阿仁哥一样,叙事主体不过是叙事客体的幸存者,是他的幽灵似的存在,是被那个或曾真正拥有的理想自我所放逐的主体。
那么可以说,这也是林阳之所以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给弟妹当家教后我爆红着回实验室
简介关于给弟妹当家教后我爆红着回实验室一心扑在实验室的盛夏晚被老爸指派回去给只想在娱乐圈里混日子的弟弟妹妹当家教。又毒舌又文盲,已经高中毕业数年的影后妹妹。又臭屁又自大,已经休学的偶像练习生弟弟。看着满屏幕拉不到底的黑料,盛夏晚很想问问老爸,这两人还要救吗?再过三个月,高考就要...
天才纨绔
分享书籍天才纨绔作者陌上猪猪各位书友要是觉得天才纨绔还不错的话请不要忘记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荐哦天才纨绔最新章节天才纨绔无弹窗天才纨绔全文阅读...
这个少妇有点儿野
...
我有一座恐怖屋
作品简介散异味的灵车停在了门口,天花板传来弹珠碰撞的声音,走廊里有人来回踱步,隔壁房间好像在切割什么东西。 卧室的门锁轻轻颤动,卫生间里水龙头已经拧紧,却还是...
明末匪事
崇祯元年,陕西大旱崇祯二年,陕西大旱崇祯三年,陕西大旱崇祯四年,陕西大旱…有完没完?还真没完。要知道这场大旱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五百年所未见。五百年?孙悟空都从五指山下出来西游了,顽石已长满青苔,沧海都变成桑田了,这么绝的事情咋就让明末陕西百姓给遇上了。灾荒时间长了,地主也没余粮,皇帝也没闲钱,不征税紫禁城就得关门。啥也不说了,该征税的还得征,陕西也不能例外。奶奶的,都这样了还要收税,让人活不?陕西百姓经过一番深入的思想斗争,联系一下当下国内的基本形势并结合本地区的区域特点,广大民众决定起义,理想远大的当起义军,理想一般的当土匪。好了,大环境就这样,提起刀开始干活吧!小说交流群号456361o91各位书友要是觉得明末匪事还不错的话请不要忘记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荐哦!...